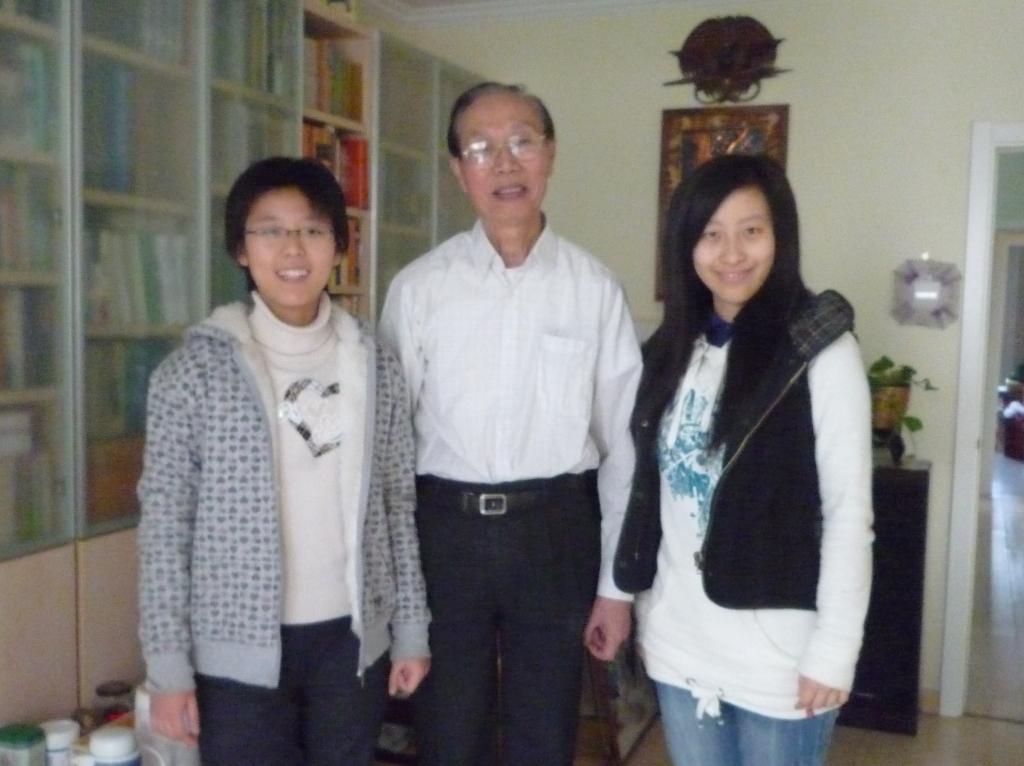采写 沙晗汀 邓明月
在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有幸在毛国华先生家中采访了这位当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我校校友。在他的客厅里,书籍占了几乎整整一面墙,书籍的内容从法律到新闻,从文学到书法无所不包。毛先生为我们谈到了他们这一届同学的一些生活片断。
苟利国家生死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们这批495名同学大多在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地的中学就读,少数也有在大学上学的。当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后,他们都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参加军干校,意味着经短期培训后就要上朝鲜前线,与敌人短兵相接,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毛国华先生最初被分配到炮兵系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奔赴前线。可是一道命令,改变了他们这批人的人生。为应朝鲜前线急需和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翻译人才,中央军委决定在参干同学中选调有一定文化程度的500名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突击学习外语。
那时,北外的学习条件异常艰苦,没有课桌椅,没有教学设备,甚至连生活用品都很短缺。学校发的一个马扎,一套棉制服和一副碗筷几乎就是每位同学刚进校的所有家当。北京的冬天很冷,学校发的棉鞋、被褥和草垫不能满足每个同学的需要,但是同学们都相互谦让,共青团员自然率先示范。毛先生就是穿着一双从南方穿来的“力士”牌胶鞋过冬的。是朝鲜前线志愿军的英勇捷报,是北外师生干部团结友爱之情消融了北京的严冬。系主任吴刚同志怕南方来的同学不会生火炉,不是怕火炉灭了同学们挨冻,就是怕煤气中毒,于是常常半夜里到学生宿舍去巡视;助理员翁斯玉同志见毛国华经常在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她就偷偷地把毛叫到她的宿舍里让他围上她自己的一条围巾;杨树勋老师见毛国华要外出实习,去陪同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访华,他便主动借给毛两条西服裤子,因为那时同学们只有学校发的穿旧了的制服。外国老师更辛苦,那时教材和教学设备都很缺乏,外国老师就承担起编写教材的重任,课堂上老师同学都是口口相授,连一架录音机都没有,下课以后,同学们又围着外国老师去练口语。伊莎白老师不仅课时很多,还要抚养年幼的麦克,可是她还要抽出时间在课余辅导毛国华的口语,因为他的家乡音较重。夜晚经常停电,无法上夜自习,同学们就在月光下三三两两地背生词或作口译练习。“当时,我们有一句口号:‘记住一个生词,就是射向敌人胸膛一颗子弹。’”大家革命热情都很高涨,人人要求进步,申请入党入团,动机也很单纯,只是一心为革命,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为个人私利似乎是可耻的。同学之间经常谈心,交换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谓推心置腹。课余以“劳动卫国”制为标准的体育锻炼热火朝天,各种文体活动也很活跃,充分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毛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奠定了人生的基础,它集中体现在北外熟知的一支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永远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我们人生的航标。”在参干60周年的时刻,他代表495位参干同学,把他们对母校的真挚感情铭刻在一颗寿山石的印章上和献给母校的一首诗中。
沉浮不改报国心
从北外毕业后,他们这批同学都毫无例外地服从组织安排,分配到外事、新闻、教育、军事、政法、经贸等各条战线,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甚至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一辈子。须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不多,可是在强调家庭出身的年代里,他们有的同学就被分配到当时看来并不“吃香”的岗位上去了,或到基层去当中学老师。然而,这些同学并不自暴自弃。他们这批分配到外交部的同学中有不少去当信使,一年365天,大部分是在飞机上度过的。那时的飞机安全系数不高,遇到空难报警时,他们首先要处理掉绝密的文件,而后把生的希望让给同伴,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驻在国排华时,使馆人员首当其冲;在西藏自卫反击战中,山下穿单衣,山上穿棉袄,每天忍着强烈的高山反应,从山下爬到山上去战斗。毛先生文革时期到北京门头沟原始矿井去挖煤和劳改农场进行劳改审查。他打趣地说:“从直不起腰的掌子面背着一袋煤出来时,除了眼白和牙齿是白的,其余都是黑的。”三月的北京,还是春寒料峭,水田里还结着薄薄的一层冰,可是他们就得赤脚下水田去播秧。1月的严冬夜晚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可是他们在打谷场上,只穿一件单衬衫还汗流浃背。尽管这样,毛先生还是非常乐观和自信,相信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终于,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又重新被起用。毛先生回顾一生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才能是相对的,人的机遇是重要的,人的功绩是渺小的,唯独人的精神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老骥伏枥志未已
毛国华先生说,他们这批同学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退休了,他们虽然两袖清风,但却生活得很充实。退休后,好多同学继续做些有益的工作,有的在社区里义务教英语或组织文体活动;有的为老干部活动中心做志愿者;有的在群众团体中担任领导工作,做些社会公益工作;有的为家乡脱贫致富,引进资金和人才还有著书立说的。退休以后,毛国华把工作看作是锻炼身体,他自参加工作以来很少在晚上12点之前睡觉,退休以后,也还是保持着这种习惯。退休以后,他曾组织一些专家、学者为拯救黄河断流,解决北方干旱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赴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实地考察,向中央提出建议,除自筹一些资金外,甚至拿出了他们老两口积蓄的47万元;以后又组织一些专家学者赴东北考察,召开座谈会,建议中央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也为内蒙库布其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尽了一点力,向温家宝总理反映过情况等等,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采纳。为了节省开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午就在办公室吃一包便宜的方便面。
毛国华说,我们这批同学总有一个信念,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毛先生出生在浙江奉化一个翠竹环抱、一涧中流的山村里,从小他父亲就教导他做人要像竹子那样有气节,宁折不弯,竹子长于脊土,用处很广,它取之甚微,予之颇丰,记得郑板桥在画竹后题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毛国华也深深感谢母校的教育,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日后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