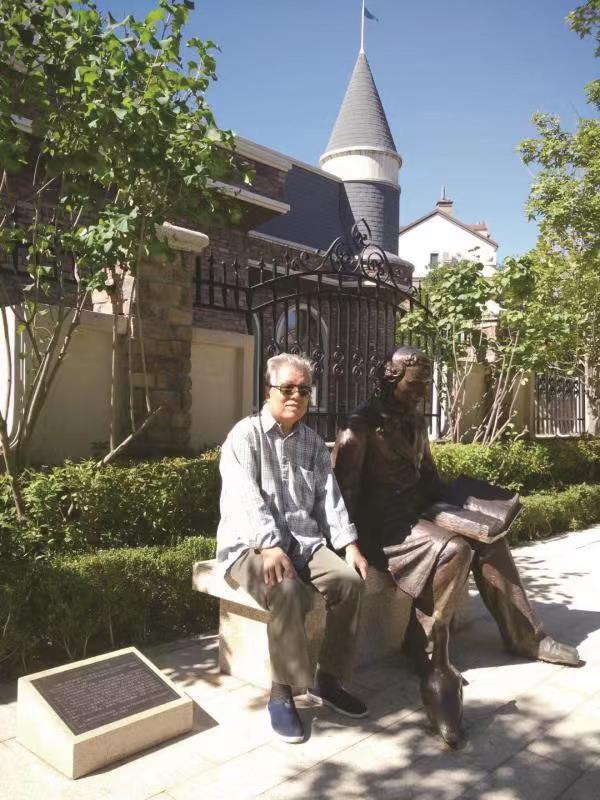
人物简介:
王洪起,我校欧语学院阿尔巴尼亚语专业1961级校友,新华社高级编辑,从1969年开始,先后四次、共22年在新华社地拉那分社工作,任记者、首席记者,并兼马其顿首席记者。作品被选入《新华社优秀通讯文集》等,主要著作有《山鹰之国亲历》、《陨落的双头鹰》等;现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外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首师大文明区划(巴尔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个阳光和煦的清晨,笔者有幸到王洪起校友的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他将自己在与新闻结缘的二十余载时光里的得失与追寻向我们娓娓道来。
从结缘北外到新华社:不为人知的爱国情怀
1961年,王洪起校友从天津塘沽农村一所中学考入北外阿尔巴尼亚语专业。“高一高二的时候学校里开设俄语课程,当时学生都不想学习外语,学校取消了高三的俄语课,而我对外语感兴趣,便继续学习俄语。”正是怀揣着对外语别样的兴趣,王洪起决定报考外语专业的大学。而那时参加外语考试的人极少,一个考场里只有两个人。当笔者问起为何要选择阿尔巴尼亚语专业时,王洪起笑称这只是偶然。时年正值北外阿尔巴尼亚语专业开设的第一年,该专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是个冷门专业,大家都没什么学习基础。于是,王洪起等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批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的学生。刚开始学习阿尔巴尼亚语的时候,王洪起遇到了许多困难。北外第一次在开设阿尔巴尼亚语专业,没有任课教师,加之王洪起的俄语基础薄弱,学习中的困难更多些。
语言学习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国内学习由于欠缺必要的语言环境,学生经常会遇到“听不懂、表达不出来”的问题。为了学好阿语,当时的王洪起每天都早起,去晨读园练习发音。“当时正值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别的专业的同学都对我们很羡慕,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进入大三之后,阿方代表团和中方代表团频频互访,需要大量的阿语翻译人才。王洪起是阿语班上第一个被抽中为阿方代表团陪同翻译的学生。起初他很紧张,担心自己的翻译水平不够格。一次他在全聚德陪同阿方代表团,领导给代表团配备了一个俄文翻译和一个阿文翻译,“当时的体委副主任问阿方代表要用俄文翻译还是阿文翻译,阿方代表希望配阿文翻译,然后我这就上了场。”王洪起的表现出色,但是毕竟初出茅庐,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不会的词汇,所幸有俄语翻译在场,做了补救,阿方代表也听明白了意思。“这次的经历既是一次激励也是一次挑战。所幸领导对我很宽容,翻译任务结束后表扬了我的工作,还鼓励我大胆翻译,好好学习。”到了高年级之后,王洪起接到更多的翻译任务,涉及各个领域,他的翻译能力得到了提升。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翻译是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代表团访华,“我很荣幸参与了此次的陪同翻译工作,因为年轻,还不是主要翻译,只能打打下手”,王洪起笑称,“但是这却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眼界。”对于该级别的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出席,周总理常陪同参观,王洪起有幸目睹了两位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一次在哈尔滨举办的宴请上,周总理看到了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吧”,能和总理面对面,我感到十分幸福,也觉得要继续磨砺自己的水平。”
当被问及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外交部工作而选择去新华社工作,王洪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实就是祖国的需要。我毕业时正值文革阶段,那时国家注重宣传,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国家宣传机关需要大量的人才。新华社要人,我就被选中了。”从那时开始,王洪起开启了在阿国从事新闻翻译工作二十余载的征程。
四赴山鹰之国:见证中阿关系的酷暑与寒冬
毕业后的王洪起进入了新华社参编部任职。因为之前他从未接触过新闻传媒,新华社于他而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他开始跟着老一辈记者学习新闻写作的技巧,负责翻译从阿尔巴尼亚传回国内的新闻稿件。1969年,王洪起赴阿尔巴尼亚负责在地拉那的新闻翻译工作。时年正值中阿关系的黄金期,大量的新闻稿件急需翻译,而地拉那分社仅有王洪起一个阿语翻译,因此任务艰巨。“那时候没有传真机,就是背代码,发电报回国,”王洪起谈到,“但是很多我们发回国内的新闻消息都没有公开报道过,因为这些信息不能够公开,只能直接反馈给中央,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消息。”在信息不发达的六十年代,中央领导获取阿国新闻消息的渠道主要是中国驻阿大使馆,再者就是通过新华社。“当时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国内的报刊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一两句。我们所报道的动乱背后详细的起因、经过与后果,都悉数的传送回党中央,领导再根据我们的反馈制定对阿政策。”
1969-1975年是王洪起第一次赴阿,也是中阿关系的“酷暑”期,而他第二次赴阿时,却是中阿关系史上的“寒冬”期。1975-1978年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中国对阿经济援助的削减,中阿关系开始急剧恶化。1977年7月7日,阿方发表了一篇《反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长篇文章来批判中国,这也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分歧公开化。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新华社驻阿分社的规模不断缩小,直至1980年,总部决定关闭地拉那分社并将阿国所有的新闻记者悉数撤回国内。1981年,阿尔巴阿尼亚总理谢胡自杀,而国内却缺乏相关报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在会议上询问国内没有相关报道的原因,“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已经没有新闻记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社出于种种考虑把我第二次送到阿尔巴尼亚,负责重建地拉那分社。”1984年再次回到阿尔巴尼亚的王洪起,遭遇了“冷板凳”。“第一次去时,外出采访时,处处受到热情接待,第二次去的时候都叫我们’特务’,连我们的记者证都不被认可。”当时驻阿外国记者仅王洪起一人,重建分社的任务艰巨,王洪起获取信息的渠道遭到封锁。每每出行,车后面总是跟着一辆阿方内务处的车,坐着便衣警察,一方面监视王洪起等人的采访行为,另一方面将阿国的百姓与他们隔离开来,避免一切可能的新闻来源。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王洪起只能通过收听阿方电台,收看电视台的新闻,记录各种有用的消息,同时加强与东欧各国驻阿新闻官员的联系来进行工作。”
90年代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局势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1992-1997年期间,王洪起第三次赴阿以了解阿国发生的政治巨变。“阿尔巴尼亚在政治领域的转型是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打砸抢烧’,而并不像是捷克等国的和平演变。”王洪起谈到,“我认为穷则思变,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应该做到变而不乱,尊重人民的选择。”当时的阿国,社会动荡,国家行政机构涣散,中国驻阿使馆只留少数外交官和工作人员,而王洪起则坚持留在阿国继续向国内报道阿尔巴尼亚的形势。
2000-2006年,王洪起第四次远赴阿尔巴尼亚。“就是国家需要我,我自己也觉得能搞出一点东西来,能继续为祖国的新闻事业发挥余热。”此次赴阿,王洪起还负责了新华社马其顿分社的监管工作。“我就希望多干一点事情出来,去深入了解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局势,而不只是一个国家,我们的视野总是要开阔一些的。”
王洪起多次赴阿,在他从事新闻工作22年间,一共十进阿尔巴尼亚,四次常驻,也是中国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时间最长的人。谈到这份坚守,他谈的最多的就是责任与奉献,“我觉得这就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所谓“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不过如此。
山与山不能相遇,人与人终能相逢
在赴阿20余载的时光里,王洪起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5年他第二次赴阿正值中阿关系的“寒冬期”,因此他的新闻采访工作也受到了阿方内务部便衣刑警的监视,而王洪起对此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的车总是跟在我们新闻车的后头,这其实也是一种保护作用,因为没有人敢动我们。”他们每逢外出采访,内务部的车必然跟在他们的车后面,时间一久,王洪起跟这些“便衣警察”也成为了好朋友。有一次在阿尔巴尼亚南部进行采访时,因为南部多山,山路崎岖坎坷,都是石子路,他们的车在半山腰突然停驶,王洪起只好找到后面跟随的内务部的车。“我向车中的三个人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车开不动了,车中三人立即到我的车前检查,其中的一个人趴到车底下,才发现汽车的机油箱被石子击裂,机油全部泄露,然后他们找来一辆卡车,拖着我们的车一路离开南部地区。”谈到这段趣闻时,王洪起微微一笑,“快到首都地拉那了,那群便衣警察就对我们说:‘回到首都之后,咱们见面装作不认识吧。’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
还有一次,正值阿尔巴尼亚遇旱情,王洪起等人亲自驱车到北部地区,考察北部地区玉米地的玉米生长情况。“我们几个去地里看的时候,有三个阿尔巴尼亚的农民跑来给我们送西瓜,他们说中国人帮助他们修了好多工厂,他们很感激。他们把我们的后备箱装满了西瓜,说是送给使馆的工作人员吃。”谈到阿国淳朴善良的人民时,王洪起总是面带微笑。“这就是民意不可欺。政治层面再如何动荡,民心是不会变的。”王洪起与阿国前任总统阿利雅是要好的朋友,在他卸任总统之后,王洪起曾经采访过他。“后来他就入狱了,那之后我还时常联系他的家人。他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我,并且表达了他想来中国的心愿,只可惜最后没能实现。”后来,王洪起特地邀请阿利雅的女儿和女婿来华,也算了结了他的心愿。
不做大家,但做专家
谈起驻阿经验对于人生轨迹的影响时,王洪起首先谈到的就是踏踏实实做事、甘于奉献的精神。“有些人觉得阿尔巴尼亚就是个小国,看不上,而你却得在那里干一辈子,得有一点信仰。”王洪起认为,自己学习阿语,并且能够学以致用,干出了一番事业,这已经让他很满足,同时,他也是研究阿尔巴尼亚问题的专家。在去年中国记者节,新华社的《新闻业务》杂志推出了八位德艺双馨的优秀退休新闻记者,王洪起名列其中。“新华社评论我是驻小国的大记者,这其实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我希望不做大家,但做专家。”
王洪起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新闻事业。在与新闻结缘二十余载的时光里,王洪起多次赴阿,和家人聚少离多。颙颙昂昂,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在与王洪起的交流中,笔者被他的见识与胸怀深深打动。光风霁月,胸怀洒落,为人君子,理应如此。
撰稿人:胡宝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