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吴培基校友
人物简介:
吴培基,1935年生于天津,1953年至1957年于我校英语系学习,毕业后曾任国防部总参谋部第三部教官,在总参机关任教近卅年,后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为北京医科大学)英语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外语部英语教研室主任,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公派英国学习,参与翻译《The Merck Manual》(《默克诊疗手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园里尽显北方的萧索。“CIAO!”一句热情的意大利语问候,伴着室内铺面的暖气袭来,吴培基教授,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爷爷,拖着缓慢的脚步,给笔者冲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我们从意大利歌剧聊起,语言的共性让我们很快便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吴培基将他与北外冥冥之中的缘分娓娓道来,那魂牵梦萦的在北外的那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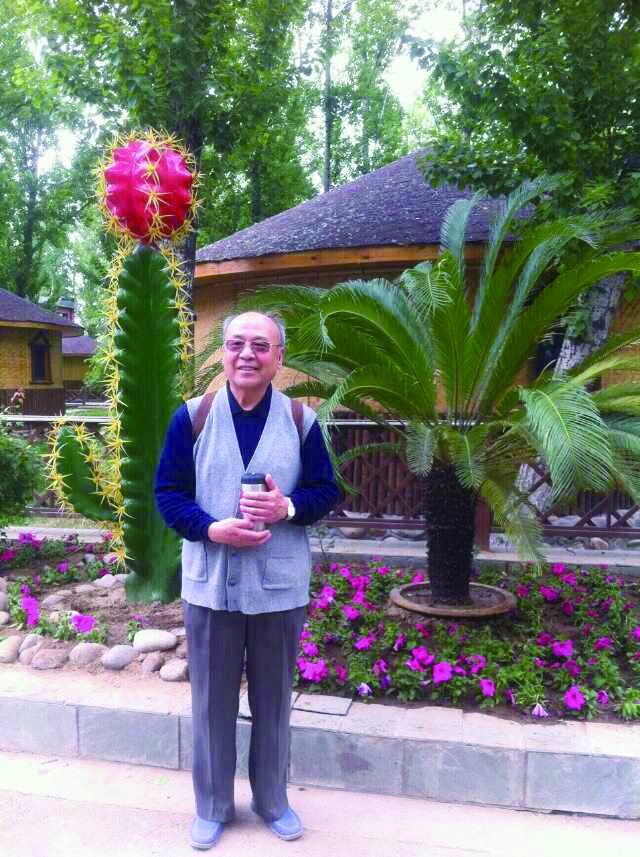
梦开始的地方
“天津新学书院看上去像是欧洲古城堡式建筑,它是英国传教士赫立德建的。书院学制四年。建筑本身仿牛津大学青灰色校园建筑,由中外资深教员任教。”吴培基语气缓慢,遥远的画面徐徐展现在笔者眼前。
吴培基的中学时代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中学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小小的剪影,学校董事们均为社会贤达,都是如顾维钧、林语堂、张伯苓等在教科书里出现的人物。
学校有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水平很高。每逢周末会有周会可以练习英语,全校充斥着英文学习的氛围。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加之吴培基的语言天赋,他的英文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
家庭对吴培基的影响也极其深刻,父亲在银行工作,而母亲因为肺结核去世,吴培基思念母亲,有志于医学,奈何因为色弱,而放弃了原本的志向。
那时的北外还叫外国语学校,只在京津沪三地内招朝鲜人民军战士,“承蒙党组织照顾,党总支书记把我喊过去,准备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给我,但后来因工作变动丢了录取通知书。”吴培基带着充满遗憾的语气,流露出对母校深厚的感情。
现在的京津城际列车,只要半小时,便可辗转于两座城市之间,那时天津到北京要四个小时。一路颠簸,到校后,开学迎新也是别有一番风貌,马扎,蓝花碗和一双竹筷,一切从简。那时的北外充斥着更多的政治色彩,从1941年建校的俄文大队起,便紧跟时代脉搏,与国家的外交动向共同呼吸。
1953年战火硝烟刚刚停下,战士们脱了军衣,便回到祖国,成为待培养的外交后备干部。当时的北外校园,坐落于颐和园西苑,那时没有食堂,只有大灶,有一条小河,在小河对面便是两层的工字楼,也就是校园的主建筑,在一楼上英语课,晚饭以后楼里便会有广播。二层是朝鲜留学生,条件极其艰苦,没有暖气和卫生间。那时吴培基负责管理留学生,虽然他的两位朝鲜室友来北外之前学了八个月中文,但他们仍坚持用英语交流,只为创造一个更好的语言环境。
四年弹指一挥间
梅贻琦有云:“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让吴培基记忆犹新的莫过于浓浓师恩。
“陈琳老师深入同学中,平易近人,每逢北京同学回家了,他晚上就不走了,睡在他们的空床上和同学们聊天,他讲话都是英式英语,编写大学英语教材。”在吴培基看来,他们当时一年级的英式英语教学颇为重要,只要打好语音基础,以后的学习便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之后可以辅以字典进行学习。
吴培基滔滔不绝地说着往事,以前的恩师们被鲜活地还原。
“王佐良教授是40年代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的研究生,新中国成立之后,硕士毕业他毅然决定归国,为我们主讲莎士比亚的讲座,相当通俗易懂,培根的《Of Study》在王教授的译文中体现出中国的哲学观点,很古朴,加了文言。”正如这篇著作中所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在中西交融中,体现出学习的普适性。
1953年留英归国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张振先教授,在吴培基印象中,他讲起话来像一个大风箱,教导学生学会用“狗喘气”的方法发音,气沉丹田,以至于现在吴培基在偌大的阶梯教室中,屋子里没有麦克风,也可以游刃有余地侃侃而谈,吴培基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成了主任医师了,他们经常提起,英文可能忘了,但老师教的歌还记得。《老黑奴》中“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吴培基认为:“倒装先行,歌是有声的诗,诗是无声的歌,诗歌是英语教学的一部分。”
现在的北外西校区专家楼前,西边角落里有一座中式的小亭子,边上写着梅洁亭,落款是冰心先生。“陈梅洁(Margaret)教授当年因为热爱中国就留了下来,解放初期她是北外长期任教的四位外籍专家之一,她为课文录音,进行语音教学。仁慈是吴培基对陈梅洁恩师最深的印象。
1949年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初大告教授担任外国语学校的英语系第一任系主任,他经常串教室,对大家的语言发音进行指正。“s”发音窍门在于,当气流通过牙齿的时候要带有口哨的音。吴培基对这个小细节记忆犹新。
用的是老师自己编写的油印讲义,精读用苏联编写的教材,泛读很浅近而上口,与其说是图书馆还不如说是陈列书架的阅览室,冬天在室外叶落的树前大声朗读,听力设备很紧缺,没有录音机和磁带,苏联钢丝录音机很结实,可以回放,一小组围坐,由老师操作这金贵的进口器材……
四年如一日的坚持,四年如初见的热爱,吴培基谈到母校时,脸上一直泛着笑容。
去到人民需要的那里
吴培基说,毕业了,赶上了要写大字报的时候,打断了学习进度,但并没有对四年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干扰。毕业时,都是服从国家分配,他没有进入外交系统,而是被分配当教官,因为部队亟需外语人才。
“我们勇敢地走向岗位,永远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情到深处,吴培基应着高涨的情绪唱了起来。
中国解放军需要与国外交流,作为教授军人英语的老师,吴培基需要结合军队内部需要,这与外交词汇不完全一样,但也离不开普通英语的模式。在部队,要做无名英雄,低调而不张扬,期间,他参与了东北嫩江的解放军基地开辟,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培训新生,在四川待了八年,直到1986年,吴培基在总参部队第三部已工作了近三十载,恰逢当时邓小平同志裁军一百万,他与爱人来到了北京医科大学,继续开始教书育人的工作。
来到新环境之后,查字典找专家便是吴培基的常态,翻译《默克诊疗手册》的临床药理学部分,这是极其枯燥和理论化的,其中牵涉到拉丁文及中药特殊名词。但吴培基认为,学习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无论是军事系统还是医疗系统,都要努力钻研,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
吴培基兴趣广泛,他加入了北医教授合唱团、北医外文合唱团,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教授合唱团,并担任副团长。他还参与了1999年的国际老年节“永远的辉煌”大合唱。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退休后,他将自己的晚年称为“玩年”,报名参加了书法班,现在已愈13载。
吴培基认为进入工作以后要向老同志学习,分配到具体的系统需要结合具体任务深入钻研。他表示,虽然没有直接搞涉外工作,但培养的将军走向国际。他感到无怨无悔,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感恩母校对自己的培养。
在意大利语中,“Ciao”既有你好也有再见的意思,《Bella Ciao》是吴培基最熟悉的歌曲。告别了吴培基校友,这位谦虚好学的“玩年”教授,他的人生大书让笔者深深回味......
(文 胡尧)
